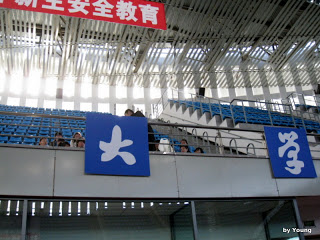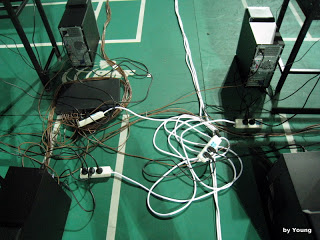穿过森林和河流我终于出来疗养了。此前决定的时候,张健和郑蕊问到,老师你啥时候回来。我
说,我不回来了。后来想起跟包师弟讨论过的一个笑话。我说,城市的街道经常
使用其他的城市命名,其实那是为了穿越。你在长春的'北京大街'上,大喝一
声'我要穿越',一下子就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天津大街 (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条
街),大喝一声'我要穿越',然后就到了天津。包师弟说,这招在德惠就不行了。
因为德惠只有一条街,贯穿整个城市,这条街的名字就叫'德惠'。所以,你只能回到那里,再也无法离开。东汤镇,只有一条街道,名字叫做东汤街。所以,我永远也穿越不了啦。不过,
我宁愿如此。街道上很多慢慢行走的人,他们大都是来泡温泉的游客,老头老太
太居多,花白的头发,颤颤微微的。还有穿着各种冲锋衣的年轻人,三五成群。但是你还是能很容易认出我来。因为只有我抱了一瓶啤酒,走两步喝上一口。从
镇这头走到镇那头,刚好喝完。卫老师说,抓一把瓜子,刚好把镇子走个对穿,
差不多。二猫妈拎着一斤半栗子,那是跟不认识的游客在小摊上拼的,满三斤一
锅,在爆米花机里添上一些水,然后放在煤火上转,风箱吹着火苗子忽忽的。这
些栗子穿过镇子的时候两个人吃掉大半。在这里,可以用吃掉多少东西来度量时
间和路程。不像来时的路,是用里程和车站的名字度量的。不过,那是昨夜,半夜的时候还
听到同车的一些家伙张罗着喝酒,那是午夜12点刚过的时候。今天早晨醒过来的
时候,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人们小声地说着话。一个女声说,凤城快到了。一个男
声数落着她,就你嗓门大。还是那个女声,用耳语的音量又重复了一遍,凤城快
到了。我爬起来,窗外,已不同于昨天的黑夜。静静的河就在车窗外面,阳光从河流的
波纹上反射出来,明亮的光变得一层一层地抖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陡峭却低
矮的山横在眼前,上面涂抹满了暗绿和暗红的色调。车行不止,突然就会在哪个
山坳里看到亮白色的建筑、高塔、管线。那是不知道做什么的工厂,在山丘的衬
托下,就像玩具,像即时战略类游戏里的场景。就这样,我穿过森林,穿过河流。从凤城火车站,坐15元每人的出租车,半个小
时,风驰电掣一般,一路上还听司机小伙讲这里或者那里发生过什么样的车祸,
然后就到了东汤镇。一整天,就是找好吃的,吃好吃的,泡温泉,研究怎么泡温
泉。晚上,街灯昏暗。窝在被子里看碟。对了,我去镇上唯一的联想专卖店买了根
SVGA线,还有音频线,把计算机接在了宾馆的电视上。今天,完成了以前没看完
的《第七封印》,还有新看的一个,《非洲皇后号》。在《第七封印》里,理想主义者救了平民的生命,平民给了理想主义者信仰存在
的理由。他们,和其他的各种人,穿越了森林,迎接了各自的命运。有的人沐浴
在灿烂的阳光下,有的人,在死神的带领下,跳着庄严的舞步。在《非洲皇后号》
里,传教士的老妹妹和一个半掉子船员计划驾着一艘破船去炸掉敌人的军舰。他
们穿越了暴风雨的夜晚、湍急的河流、看不见河道的沼泽。我非常想知道,然后
呢。我们也穿越过很多河流,穿越过很多森林,也许前面还有很多。也许,我们会停
在哪里,比如,停在一个无法穿越到任何别的地方之处,比如,在大海与沙滩之
间。比如,我总以为自己一直停留在1979年,此后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都是遥
远的未来。你呢,你停留在哪里?--------------------博客会手工同步到以下地址:[http://giftdotyoung.blogspot.com][http://blog.csdn.net/younggift]
Month: October 2012
师大净月校区
ACM-ICPC 2012 长春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2012 长春。
照片传不上来了,可以在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79209115/] 看到。
ACM-ICPC 2012 长春.准备 2
ACM-ICPC 2012 长春
夜雨,夜曲,及乱七八槽的其他
夜雨,夜曲,及乱七八槽的其他我终于决定得去疗养一下了。张老师说,你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blabla。我靠在窗户旁边,一个劲点头。同学们正里里外外忙活着拆机器。机房里尽管开足了灯,还是有些阴暗,我眯着眼睛一直看窗外,阴天,但是从阴暗的机房看出去,外面好像闪耀着白茫茫的光。今天一早的路上,我清晰地听到手机玲声大作。乱翻衣服,找出手机来,没有来电。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幻听。其实也好解决,我一整天把手机握在手里,听到玲声的时候就看一看。视觉和听觉一起相互佐正,就容易判断什么是真实。不过,我想我是得去疗养一下了。说起疗养,我最先想起的是挪威森林。看完这部片子的第二天,发现所有的视频网站里大部分日本影片都消失了。片子和原著都提到女主角直子疗养的地方,似乎有茂盛的森林,平缓而高的山,好像还有山泉。直子没有痊愈到离开那里,很多鬼子的作品都这样,让人看完了也想跟着自杀,不过他们的人口好像也没见少。无论在山林间,还是在城市里,他们都没有找到自己,只是试图用貌似狂热的行为确认自己的存在。很多鬼子的作品都这样,让人看完了想自杀。工作于我,也是这样。我正把自己拆成一行一行,涂抹在代码里。在那里,我就可以一直存在。存在到你们都死光了,然后爬出来给你们大家写传说。我最得意的事情就将是,后辈小生们任谁出无法否定我写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我可是亲眼所见'。昨天夜雨,关着窗户也能听到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连绵不绝。从暑假唐山回来,腰间盘就一直没有好,而且每天忙碌。忙到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有几天,甚至得换成平板电脑才能计划日程,因为纸上实在是放不下了。常常放下电话,然后接着再打下一个,跑到哪里见谁谁,然后再电话,再见谁谁。生命被切割成碎片,也就没有连接在一起时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痛苦,至少你无法看到不一致,所有的面孔都一闪即逝。然后,下一个。唐山回来以后的另一个特点,我看到下雨就开始发抖,不由自主,难以控制,是因为这次腰突发作正是因为早晨一场凉雨。而今年东北的秋天,似乎也不怎么缺雨水。滴答,滴答。因为腰不能负重,我走在路上的时候,需要二猫妈替我背着包或提着东西了。在应化所,我看关同学去把显示器抱过来,哎哎哟的,我也无能为力,不敢伸手。大家搬机器,用键盘设置机器环境,我坐在那里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蜷缩在椅子里,隐约地看着显示器的光,我说,你们整吧,我得歇会儿。抑郁,是件长久的事。得接受它伴随终生。偶尔有些阳光什么的,千万别以为那才是长态。我们都沉在海洋里,仰面望着天空那一圈光亮。有些人沉得深些,有些人沉得浅些,但是,没有一个人浮出水面。所以,深或浅也没有多少区别,大家都很可怜。十一长假,我毕业的学生们跟我聚会了,送我的礼物有用来填肚子的,也有用来填脑袋的。关同学送我鲁宾斯坦弹奏的肖邦全集。她说,肖邦最大的特色就是憋屈。我说,恩,跟我挺对路。跟他们长谈以后,我的嗓子越发完蛋,日益沙哑。所以不少人发现我说话明显变慢了,为了清晰起见,也明显变少了。其实,我连这些也不想说,我想沉默,也想闭上眼睛。这样听肖邦。夜雨,夜曲。我摘下眼镜,看到千百个世界重叠在一起,溶化和破碎。我就这样裸眼,在屋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如果你记住所有陈设的位置,就很容易不碰翻任何东西。
那天下午,讲课。我没开投影仪,黑板上只写了几个字,学生有点少,教室里显得有些空,讲课的时候略有回声。我讲了模块化,信息隐藏,接口,契约,责任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SICP这一节背后的意义。为避免其他专业的某些同学误解起见,补充,与东方哲学相信的不同,在工程中,信息隐藏并非恶意,目的之一为了调用者考虑,避免记住大量无用信息的负担。有几个同学在偶尔记录,大部分同学以一种有些惊讶的表情半张着嘴从头听到尾。你们也许在想,工程和世俗的生活,会有一致的地方么?是的,它们是一致的。我们用工程的方法生活,用生活的态度工程。这些,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契约可以不遵守,那么契约为什么需要存在?如果契约不合理,我们应该做的是修改契约,而不是破坏契约。接口设计的根本原则是清晰、简洁,而不是其他的。接口明确地规定了模块的责任。工程师正是因为承担责任而存在,这个时候,他们所体现的是像工具一样的效用,而不是人性。我们作为对方的工具而存在,彼此。工具的特性非常雄性化,其基本要求是
可靠。萨特说的,你因为你的行为而成为某一种人,而不是因为你所说的或希望的。对了,似乎在场的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萨特。黑板上只写了几个字,我就这样望着虚空,絮絮叨叨地讲这里讲那里,大系统模块间的协作及工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我要说的太多,有的时候,一分神,就得问大家,我刚刚在讲的是什么。然后在继续下去,那些工程与生活相同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从生活中理解工程的地方。我知道,听到的人就会听到,不听的人就是听不到。大家都望着虚空,跟我一样。不同的是,你们有的人会说,我会看你的每一篇博客,都很喜欢,非常有启发。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一种感情表达,一种表演,'你瞧,我对你多么友好。'根据有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微笑感谢,假装相信;根据萨特的观点,也许我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还是会写:因为如果不是想撕裂嗓子一下大吼,那么我希望沉默,一个字也不说。--------------------博客会手工同步到以下地址:[http://giftdotyoung.blogspot.com][http://blog.csdn.net/younggift]
铁子同学,我的理想
铁子同学,我的理想这个你就不用猜了,铁子同学,写的就是你。铁子同学说,你能不能不叫我的全名,叫我铁子或者啥的。我解释了一下,在我们那个时代,甚少称呼别人的名,太亲昵或者暧昧。不过,愿意遵从他的愿望,从那以后,我就称他铁子。他叫我老杨,问我,那我能叫你老杨吗?我哈哈大笑,当然可以,我从小学的时候别人就叫我老杨啦。他说,真的吗。看来他没有学过《老杨同志》那篇课文。铁子同学,全名张铁子。这样的名字比较有文化--尤其是相对于杨贵福这种偏远山区五六十年代的常用名而言,有文化到我都不知道怎么读。那个'子'字到底是轻声,还是三声呢。我第一次接到铁子同学的电话的时候,他自己先读了一遍,'喂,我是张铁子'。他发的是三声。不像我,我在电话里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也读的三声,福,但是,那是错的。读对的人没有几个。然后我就说,啊,是你啊。咱们约个时间吃饭吧。吃饭也就是吃饭,还有吃菜,我已经不能喝酒了,虽然跟铁子同学吃饭真是件当痛饮的事。比如,他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他的理想。他打算坐欧亚大陆的列车,穿过西伯利亚。他开始给我历数列车将要停靠的站点,那一系列俄罗斯名字。我差点以为对面的是亿万星辰大哥,他修俄语的。跟亿万星辰大哥一样,铁子同学也是黑龙江人。他给我讲过广袤无垠的三江平原,他的故乡。他说,我们那不是市或者县,而是什么什么建制,类似于屯垦兵团的编号。他从小的时候从市中心向外走,走了很远很远,还是路,后来看到了...我的印象里是类似于《太空漫游》里的黑石柱一样的东西。当然,我的记忆可能是错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是在听铁子同学说,而是在听青年的自己讲述自己的理想。只是,他满脸都是憧憬,我满心都是悲哀。所以,和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问铁子,你开始准备徒步乌苏里江了么?他诧异地说,是啊,当然,我已经徒步过了啊。我说,啊?这么快。他说,我家就在乌苏里江旁边啊。我才想到,那不是他的理想,而是我的。我想徒步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穿过黑得不透光的原始森林,坐在岸边阳光晒得烫人的白色大石上,听江水和松涛轰鸣。我还问过铁子同学,乌苏里江有堤坝么,边防部队允许我们接近界河么。网络上传说,在极北的地区,大江没有堤岸约束,漫山遍野地流淌,动辄漫延几十里,一眼望去,浑无边际。我想沿着这样的河,一直走下去。曲曲折折而不改所向。我想背上相机,沿徒拍摄,然后发在博客里显摆。我想在午夜里听风或雨掠过帐篷。就像铁子同学准备驾着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我们的世界里所有寒冷的来源。但是,我不能再远行了。我担心很多。我担心,如果什么东西掉在地上,腰间盘阻止我弯腰,大家都说这时应该曲膝下蹲。但是事实上我的膝盖下蹲也遇到了困难。我甚至开始忧虑在那种环境下怎么上厕所的问题。这是我在铁子同学的这个年龄从来不屑于考虑的话题。但是,当我与同事讨论的时候,我们很严肃地说,是的,那非常有困难,我们甚至没有揶揄的表情。时间,把我们扭曲到可以接受这一切,如同那就是本来的样子。而铁子同学,仍然怀着理解。更令人嫉妒到恨的是,他的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铁子同学说,我一定要坐火车去西伯利亚,如果坐飞机从天上看,那就没意思了。我期待你从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发来消息,说你遇到一个俄罗斯的姑娘,美丽,大方,最好还能说英语或者汉语。然后你们在那么漫长的旅途中痛饮,一起欣赏品评窗外的万里长空和沃野。如果一连几天不变的空旷让你们孤寂,那么你们就抱头痛哭吧。也许,只是她痛哭,跟你讲述如何她少年时的理想。你给她唱,'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告诉他,这首歌的原唱是在怎样的青年离世,从而再也没有背弃理的机会。也不必经受这样选择的残忍。然后在某个小站,你就平静地与她道别。像哥们一样拍拍对方的背。也许,你送他一本你签名的自己的诗集。人生,也许吧,就是这样。不过,你的人生可能与我们的该有许多不同。毕意,你是一个能到过西伯利亚的人。而我,已经不能指望漫游你小时候就走过的河了。最近的两三篇博客,贴出来几天以后,我就在午夜的时候收到铁子同学的短信。谈谈他的感受之类的。我知道,他可能只是委婉地确定我还活着呢。人生如牢狱,怎么会轻易就摆脱得掉呢。《路西法效应》是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里面有一段似乎谈到了理想,作者说:囚犯们经过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同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近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队制服。这些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者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然后作者引了一段话,"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人生的牢狱,还有着更漫长的岁月,于你而言。希望你能时刻记得,而不会忘记--你还没有到达西伯利亚,你还没有到达西伯利亚,你还没有到达西伯利亚。然后,所有的障碍,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借口,就都不会欺骗你西伯利亚已经到达,或者这个理想也没有多么重要。你的理想非常重要,它激励我这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纯粹的高远的理想。所以,真正地,这博客不是为了写给你或纪念你的,而是为了我的理想。--------------------博客会手工同步到以下地址:[http://giftdotyoung.blogspot.com][http://blog.csdn.net/younggift]
音乐,代码,纯爱
音乐,代码,纯爱回顾中国摇滚,罗琦的回来,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崔健的一无所有。想着这些歌者背后的故事,感受疯狂和喧嚣。我内心苦涩难过,眼泪却掉不下来。找到梁博的《回来》,单纯悠远。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不可遏制。当年,第一次听到Don't break my
heart,我想,听完这首歌,我就可以去死了。我当然活下来了,不然你又怎么会看到这段文字。以前,我没有听过《回来》,听梁博的演绎是第一次。他刚一开口,我知道,这不是汪峰。汪峰有落寞,却并无绝望。我查到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罗琦。音乐的力量,有的时候当场刺得你心痛,就像窦唯;有的时候,当时听到的时候内心一片平静,只是略微记下有点印象,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早就埋下种子,此刻已生根发芽,每一下和着节拍的振动都真切地牵着你的血肉,痛到骨子里。就像梁博的摇滚。我一直以为,死亡是突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个战士,像魔鬼终结者II里的液态机器人,当脚冻在地上,我们仍然努力前行,然后--啪,腿就折断了。负担没有了,我们继续前行,像魔鬼一下坚强。并不是这样。在死亡之前,有一段极其漫长的痛苦的不死的过程。然后我想起来,这位罗琦,她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她的一只眼睛在打斗中被刺瞎。这是大约1994年前后的时候读过的新闻,然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但是我仍然能精确地回忆起来。有时候,我为自己的记忆自豪。有时候,这也令人痛苦。因为它能把所有别人都忘记的东西串联起来,然后推理,发现大家想掩盖的东西。有时候,我希望我又聋又瞎,看不见听不到这个世界。这样,所有的利益当前时,大家的表演就都可以消失不见,比如舞台上选手的热切,比如被弃选后抱怨的眼神。你们,不是说一切为了音乐,只是为了音乐么。为什么,那一刻,我听到了音乐以外的声音。梁博,让我看到真正的对音乐的追求。我希望以后永远也看不到他表现出徐海星和吉克隽逸的那一面。从前,有时候我会想那些偶像们的结局,比如孟庭苇。我希望她们在最美丽的一刻死去。我们就可以老去,可以嗓音嘶哑,呼吸都困难,再也唱不出哪怕一个乐音。或者有一天,我们说,我再也不爱音乐,滚音乐他妈的蛋。但是,不要,永远不要,永远不要,永远不要欺骗。你侮辱了自己之前所有的热爱。所以,我暗自希望,梁博要胜出。至少,不能是吉克隽逸。不能是为了女朋友的金,不能是为了民族的走向世界的吉克。哪怕是像吴莫愁那样--我喜欢这样玩耍,至于你的态度并不是我关心的。一个人,喜欢歌唱。这就是全部的和唯一的原因。就像我们写代码一样。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声誉,所有那些都是副产品,有如浮云。当所有这些都没有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写代码。黑色的背景,绿色的字符。就像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眼睛看着并不存在的远方。单纯的热爱,就是当一切带来的附属都消失了的时候,我们仍然执着于当初的情感。我希望自己能实践自己所相信的。所以,作为一个高龄半音盲,8月24日,停了大约一年以后,我继续听音练耳,9月30日,结束了第一章的学习,共42课。同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腰间盘会成为学琴的障碍,需要努力同时小心翼翼的坚持。音乐结束的时候,主持人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词语,"这个夏天"。大家,把这当作自己人生中的一站,一个令自己成长的历程吧。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所有这些,都刻写在我们的人生中,成为了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崇高和卑微。感谢权振东版的《冬天来了》,感谢梁博所有的歌。谢谢你们让我流泪。感谢梁博的歌唱让我认识汪峰的北京,一个繁华以外的悲凉的世界,令人感动。感谢苏恒。谢谢你带领我听到音乐。我期待当黑暗遮蔽我的眼睛,键盘上的那些声音能唤回对光亮的记忆。--------------------博客会手工同步到以下地址:[http://giftdotyoung.blogspot.com][http://blog.csdn.net/younggift]